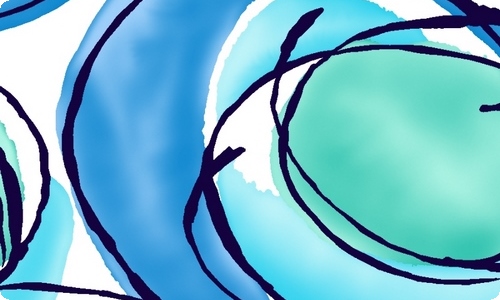比捕鼠笼大两个跟斗的铁丝笼,装着毛茸茸的小狗和小猫,三个或者四个叠成一叠,四叠或者五叠排成一堵矮墙,摆放在三中巷巷口。二贩子站在墙后,狡黠地看着围过来的小孩。
红脸膛的二贩子有一股子外地人的气味,让庞晓英很不喜欢且有点紧张。第一眼她就觉得二贩子很凶恶。又高又大的人穿着件皱了领子短了袖子缺了扣子的衬衫,露出又胖又红的肌肤。衬衫穿成这样拧巴,眼睛又是那么的闪来闪去,像在打什么坏主意。
而且她的弟弟庞蕴蹲在笼子前正一个笼子一个笼子翻来覆去地看着,这更让她焦躁。笼子里的小狗一只只都毛茸茸的,除掉几只无精打采趴着的,其余的张着乌溜溜亮晶晶的眼睛,骨碌碌地跟着他转,很温驯,很漂亮,很可爱。
庞蕴看狗看得沉浸,庞晓英着急地拉他起来,她预感到弟弟要买狗,可她不愿在这件事上花钱。她是厉喜妹的小管家,身上常有几毛明天买菜的钱。她很有职责感,对得起妈妈的信任。此刻得尽快把弟弟从铁丝笼前拉开,省得他闹。拉了几下没拉动,她暗叫不好,庞蕴这个死小孩估计已经下定决心,要买一条狗。
果然庞蕴指着铁丝笼,回转身对庞晓英说:“买条狗”。
庞晓英说:“不买”。
庞蕴站起来下命令:“买”。
庞晓英坚决回应:“不买。买了放哪里养”?
庞蕴成竹在胸地说:“家里”。
庞晓英焦躁地说:“吵死人养条狗。你不怕婆婆骂?”
庞蕴的嘴巴立即闭上。庞晓英总是很有办法对付他。
婆婆是妈妈的婶娘,三中巷靠前的那栋四合院的孤寡老人。婆婆住在他们家隔壁,左边的一间单房。每一天夜里,早寡的婆婆只要院子一有些许风吹草动——有时是他们家右边邻居的杨家婶和孙叔的那间单房的细微吱呀,有时是他们家四姐弟打闹——就会在她的房间里破口大骂,声音凄厉,语言恶毒,无的放矢却人尽鱼鳖。
曾有过一次,他们四姐弟在明确的`针对他们的骂声中仓皇地连夜出逃,躲在河边,恶毒的叫骂声在耳边的回响依然让他们觳觫不已。下完夜班的妈妈好不容易找到他们,也只能默默无语。在公社当武装部长的父亲从乡下回来,找过婆婆交涉,算是暂告解决。
父亲在还好,父亲一下乡,婆婆就故态重萌。婆婆只是妈妈的婶娘,而且听说不是至亲的婶娘,只是辈分上的,叫着的婶娘,不亲的。他们四姐弟恨死她了,但同时又怕得胆战心惊。要是养狗会惹着婆婆,那可不好。
察言观色的二贩子插嘴对庞蕴说:“这几条小狗都很乖,不会叫。你看”。他边说,边伸出一根手指插进一只铁丝笼的空隙拨着小狗们的嘴巴,小狗们只轻声的呜呜低吟,眼睛乌亮亮地一副可怜相望着庞蕴,像是在说:“我真的很乖,不会叫”。
庞蕴受到激励,提高声音说:“我要买”。
庞晓英气得鼓鼓的,庞蕴这个死小孩怎样这么听别人的话,好骗。她别过脸,不看庞蕴,不作声。庞蕴见姐姐这样,想起自我很多愿望在姐姐那里石沉大海,气愤填膺,大声地说:“上次你说给我买糖人你也没买,你还把我的钱给拐走了”。
庞蕴说的钱是他有次吃了父亲一个带着惩戒意味的小小脖拐后两天没理父亲,父亲为巴结他而给的五毛钱。当天夜里庞晓英就劝说他把钱交由她帮他保管,慢慢买糖给他吃。他将信将疑,还是给了她。一段时期过后,庞蕴没提这事,庞晓英认为他忘掉那五毛钱了,谁知他此刻旧事重提,令她猝不及防。
庞晓英又羞又恼,庞蕴在这么多人面前把她说得好像是个拐子,让她下不来台。但他说的又是真事,反驳不了。只但是那五毛钱早就贴补进了家用,除了弟弟,家里谁都明白。她问心无愧,不屑回答。可她下意识地转过脸,看到弟弟看着她的眼睛里转动着两大颗眼泪,楚楚可怜的样貌,心就软了。
她拍了一下弟弟的头说:“就明白买买买,随便你,挨骂了别怪我”。
然后,在庞蕴蹲在笼子前挑狗的时候,庞晓英和二贩子讨价还价,从两毛还到一毛七分钱,庞蕴也从各种舍不得中挑了一只小花狗。二贩子将小花狗抱出笼子递给他,他准备伸手接的时候突然担心小花狗会咬他,退了一步,一向摇头。庞晓英嘟嘟囔囔地付钱,接过小花狗,揣上找回的钱,横了一眼庞蕴,往家里走去。
小花狗买到手了,庞蕴突然害怕且后悔起来。他模糊地意识到被二贩子给糊弄了,庞晓英一接过小花狗,小花狗就露出牙齿响亮地叫了几声。这几声吠叫没表现出在笼子里被想象的友好,不仅仅杜绝了他亲近小花狗的可能,也让庞晓英刚才的警告变得越来越近于实现。